這篇論文主要介紹的是民法典時代商事立法體例的選擇的內容,本文作者就是通過對民法典時代的相關內容做出詳細的闡述與介紹,特推薦這篇優秀的文章供相關人士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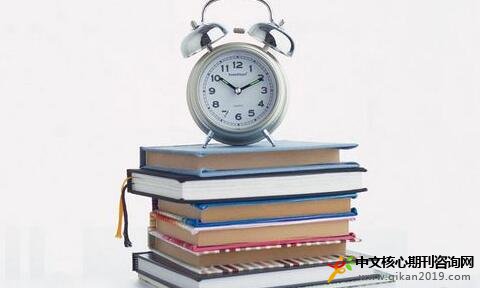
關鍵詞:商法體例;民商合一;商事通則
自清末修律至今,對于商事立法體例的探索和爭論已逾百年。商法,作為基本法律部門中與民法聯系最密切者,其立法體例很大程度上受到民法的影響和牽制。《民法總則》開啟了民法典時代,為商法體例的選擇進一步限定、指向。目前學界的爭論中,我國商法體例大致有四種選擇:一如瑞士,實行完全意義上的民商合一;二如法國、德國,實行完全意義上的民商分立;三是制定一部民法典,并另行制定商事單行法;四是制定民法典和一部總綱性的商事通則,對具體商事法律制度和關系則以單行法規范。①筆者認為,當下我國應當堅持民商合一,制定商事通則以總領商事單行法,以保證民商事立法的協調。
一、堅持民商合一的立場
(一)基于歷史的選擇
以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為分界,在此之前中國采民商分立制,此后采民商合一制②。從時間跨度上看,自1929年《民國民法典》至今已近百年,期間我國從未背離民商合一體例;其次,國民政府在百年前轉變體例,是因社會思想的進步和強化自身統治權威的政治考量,減少了全盤繼承外國立法例的盲目,更全面地借鑒了蘇俄、瑞士等國的做法,具備了更強的自主性,較清末采民商分立更為謹慎、科學,更符合我國實際需求。新中國改革開放后,我們仍選擇了民商合一:如86年《民法通則》將民商事主體和法律行為統一規定、99年《合同法》將民商事合同統一調整。《民法總則》又延續了上述做法。審視實踐成果,我國民商合一制總體上是比較成功的,這至少在事實上印證了民商合一體例的價值;同時,若繼續沿用這一體例,就立法成本而言也較為經濟。
(二)基于商法特點和中國現狀的結合
商法不同于民法,其個性大于共性,難以通過嚴謹周延的邏輯體系將其規范囊括起來,且商法所調整的社會關系變化迅速,相比“法律邏輯與概念體系”,它的生命力更在于“對營利性的商業模式和商業交易的鼓勵、保障與規制”。③對應到我國,近三十年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讓新的生產消費形態層出不窮,且變化極快,難以提取公因式,這與高度要求內容穩定、邏輯周延的法典幾乎水火不容。若當前將商事規范法典化,必將加重法律的滯后性,進而限制經濟發展、科技和制度的創新。總之,我國目前不宜放棄民商合一的體例,商事規范只能在民商合一的框架下布局。
二、制定商事通則的優勢、可行性和要點
選擇商法體例的猶豫主要源于對控制法律滯后性和統一商事單行法的平衡。面臨本就存在沖突的需求,總是難以萬全,只能謹慎地追求邊際效益。在可預見的未來,最佳的平衡必是制定一部規范商主體、商行為等基本事項的商事通則以統領商事單行法,使之體系嚴密又不似法典一般僵硬。這不僅能夠匹配我國抽象概括式的立法技術,又可以簡化規則、避免重復立法、減少準用現象;同時能適應我國商法學的教育模式及成果,立法層面的統一也有助于商法理論的進一步發展,促進未來立法的成熟。從可行性上看,國際上確無成功模式可供借鑒。但我國曾在民法規范尚不充足的情況下制定了《民法通則》,為商事通則提供了經驗。以當前立法實踐看,我國對商事活動的調控已有相當經驗,民法總則也已頒布,商事通則的邊界得以明確,此時制定商事通則至少應比86年制定《民法通則》更有把握。但在制定商事通則時,應把握以下幾點:首先,注意商事通則在編纂邏輯上的特殊性。在制定商事通則時,不能為“潘德克吞式”框架所困,避免在體系上鉆牛角尖,重要的是把握解決問題的現實需求及商法相對于民法的特殊之處。其次,需要特別注意商事通則與民法———尤其是《民法總則》之間的協調與銜接。民法和商法至今沒有精確的界線④,也更容易產生沖突、競合。商法,較民法而言是特別法。在民商合一的大背景下,商事通則應擺正位置:作商法系統中單行法的統領、作私法系統中對民法的補充。雖然制定商事通則難免導致其與民法規范的交叉重復,但這畢竟只是立法技術層面的問題,同商事單行法之間的法條疊加、沖突相比,前者是相對可接受的。這也更體現了商事通則是妥協的產物。最后,需要注意穩定性和靈活性的統一,如果不能在立法技術層面良好地平衡這兩者,商事通則也就失去了“妥協”的意義,脫離了其初衷。
作者:張嘉彥 單位:華中師范大學
相關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