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С�f����l(f��)չ���ۏ��s������Դ�c�f���ČW�������Pϵ�����Ų��ϵİl(f��)��С�f�c���x�ɷN���w(li��n)ϵ�������l(f��)�F(xi��n)������Դ���}�ă�(n��i)�ݺ�ˇ�g��ɫ�������ǧ�z�f�|��(li��n)ϵ������С�����ν�Bһƪ��(y��u)�㿼���ČWՓ�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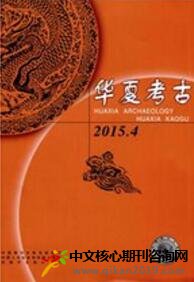
�����҇��ČW�����У����w���࣬���в������o���x���������@�ӘO��������ɫ�����w��С�f�DZ����w�б��^�����һ����“С�f”һ�~�ij��F(xi��n)����Ҋ�ڡ��f��·������˕r������һ�����w����;���F(xi��n)���W�ߵ��о�һ���J�飬�t���ƴ�����ij��F(xi��n)���Ůa(ch��n)���˽ӽ��F(xi��n)��С�f���w�ĸ����С�f����ʽ�cԊ�衢ɢ�ġ����О��Ĵ����w�����ǽ����������מ顣���������ƴ����ƴ������������g���Կ�Խ��(sh��)���꣬�Ϳ�ҊС�f�l(f��)չ��Դ����ô���ۺ͏��s��
�������w֮�g���P(li��n)�о��DZ��^�Ѓrֵ�����x�ġ������Ԏ����҂�������������̵��˽��҇��ČW�İl(f��)������Դ�Ͱl(f��)չ׃�������x���҇��Ŵ�С�f���Pϵ�о��������зdz��Ѓrֵ�����x��һ��о�������Ŀǰ�ɹ��о��Ŀ��g߀�ܴ��ăH�xȡ�����������ƪՓ����һ�C�������ˆ��}��һ�ܸQ��
����һ���P�����x�IJ���Ͱl(f��)�F(xi��n)
�����҂����y���x�@һ���Żֺ�����w�c“��”(li��n)ϵ��һ�𡣵�һ�ο��Űl(f��)���˂���һ�Ό�����(li��n)ϵ���������l(f��)���P��“���x”�IJ��롣�����I�ڡ����x�İl(f��)�F(xi��n)�����ČWʷ���x��һ����ӛ���˴˴ο��Űl(f��)��“1900�꣬�ػ�ʯ�ҳ������ĕ��У���һЩ��‘�x’��ƪ����Ʒ�������vһ�����ӵĹ��£�������Ԝ�C���Z���M���茑�����}�o�P���ν̻����Z�Դ����ÿ��Z����ʽ�������g���{��ʽ���硶�����x�������n���x�������،��x���ȣ��c���y(t��ng)���x��������ͥ��”��118�@�ο��Űl(f��)���W�����P�о��߰l(f��)�F(xi��n)��һ�N�µ����w——���x�����@���ڶػ�ʯ���аl(f��)�F(xi��n)���x�������Q��ػ����x��
�����ڶػ�ʯ���аl(f��)�F(xi��n)���@�����x�˲������x������F(xi��n)�ںΕr��1993��3�£����K�B�Ƹ��Ж|���h������hĹ6̖Ĺ�аl(f��)���˳�����20Ƭ���ϵġ�����x�����@ƪ�x�ÔM�˻����ַ��v���˴��ۃ�ֻ�B�H�߱���ɫ�ʵĹ��¡�ԓ�x�������\��������Z��������ɣ��Z��ͨ�ף��Ͷػ����x�H�����ơ���Ⱥ�ڡ��h�����x�c�Ї��Ŵ�С�f�l(f��)���о������f��“��(j��)ԓĹ������ʼ����(ǰ13��)����܇������Ԫ��Ԫ��(ǰ12��)�v�V��Ԫ������(ǰ10��)���v�V��Ԫ�Ӷ���(ǰ11��)�v�V�Ș��мo��ĺ��������Д࣬ԓĹ����r�g�����hĩ��h�ɵەr������ô������x�������r�g���t�ஔ�����h����֮ǰ��”��116
�������ˡ�����x���İl(f��)������߀��һ�ο��Űl(f��)��Ҳ���C�˝h���������x���x�Ɍ�������ӛ�����С��n�{�ޡ�����;�ڶػ�Ī�߿��������ƴ�ͨ���ČW��Ʒ�У��С��n���x��һ���������������������o30����l(f��)�ġ��ػ��ı�<�n���x>�������Ɯy�ڡ�����ӛ��֮ǰ���n����f���Ѯa(ch��n)���������g������1979�꣬���a�������ڶػ��RȦ���l(f��)�F(xi��n)�˝h�������zַ��ľ�g��һ����ӛ�d���n�i���µ�Ƭ�Ρ�����Ⱥ���h�����x�c�Ї��Ŵ�С�f�l(f��)���о����f��“�n��������ij����r������Ų����������h���ں���ç�³��ķ�����”��117�����I�ڡ����x�İl(f��)�F(xi��n)�����ČWʷ���x�����f��“1935�꣬�����������ڡ��ػͱ��n���x����һ�����Ɣ࣬���h�r�����g���������@�N���f���¡�������Z��ʹ���� ��ӛ���x�w��Ʒ��������x���ij������C�����������Ɣ�����_���������x�Ěvʷ���c������һ�l����”
���������I����Ⱥ��Փ����һ���J�飬�҂���ԓ����ҕ�h���x���Č��H��r��“�h��һ���д��������Ԓ�����v���µ����ČW��Ʒ���������кܶ���ԓ�����Թ����x����ʽ���ڵ�”�� ��117
�����������x�Ŵ�С�f���Pϵ
����(һ)��Դ���ϵ��Pϵ
������Ⱥ���h�����x�c�Ї��Ŵ�С�f�l(f��)���о����J�飬“���x��ij�N���x�Ͽ����cС�f���s��̖”��“�h�����x���H�Ͼ��ǝh�����С�f”����Ⱥ���@��Փ�C�ģ����J��������“�f�w”���Ұ���“�f”��“��”��“�Z”���;“�f”ָ�f�v���£�“��”��Ҫ���vʷ��“�Z”ָ�����¡�“С�f”����“�f”��֮С�ߣ���“�f�w”�Ё������g��“���Z”���֣�“��Մ���Z”��“�� ;�f”��“���С֪”��“�cʁ���”�������ڌm͢�е��vʷ�f�¡�
���������I�����x�İl(f��)�F(xi��n)�����ČWʷ���x���J�飬�������x�Ԕ�“��”������Փ�q���x���q“��”��Ŀ��(�Еrֻ��ҕ�q���^�̣�����̫�Pע�q�ĽY��)�����{�w���x�Ԍ�“��”����F(xi��n)�ַ���“��”Ҫ���ӣ�Ҫ��ì�ܛ_ͻ���@������“С�f”��؟�����������Ժ������x��uλ��������С�f��
�����������ڡ�̽�����x����׃ۙ�E——��Փ�ػ����x�c�����ČW��һ�����J�飬“�x�w���d��……�ɞ��˴��M�҇��Ŵ�С�f�γɵ�����֮һ”������Ԯ�����B�������ڡ��x���Ї��ČWʷ�ϵ�λ�á�һ���f��“С�f�cԊ��֮�g�����x�@һ�N�|����һ������Ԋ֮��������һ���������������������ֱ����f����Ԣ�ԣ�����С�f֮�E�x��”�����������ڡ���С�f��Ŀ�������ƴ�С�fʷԒ������Լt������c�������ԒС�f�о����У���ֱ���ػ����x�й������^�����xҕ��“С�f”����Փ����
�����K�v�ڡ����ɝh�������x�c��С�f֮�l(f��)����һ���У������x�c��С�f��Դ���Pϵ���@���U���ģ�С�f����Դ�h���ݵ��Ϲ�Ԋ���еĔ������أ���“���g����”;���t�ܻ�����Ԓ��ʷ�����T��ɢ�ĺ��x�ȶ�N���w���ÈD��ʾ�@�NԴ���Pϵ���£�
�������R����ƽ�ġ���ֲ�bٽ��(y��u)С�f�l(f��)�������^�c�^֮ǰ��ƪՓ�ı��^���أ��H����Ҋ����ֲ�bٽ��(y��u)С�f��(sh��)ǧ��֮���d�ڡ�����־·κ־������һ�����ӂ�������֮ע“������”������κ�ԡ���Փ�Ľ�(j��ng)�^�Փ�C�������g����һ�N�e�`�^�c�����˂��e��ٽ��(y��u)�����ٽ�C������С�f����ɹ��£��Ķ��e�`���J��ٽ��(y��u)С�f����ٽ��(y��u)�v�f��ЦԒ���¡���ٽ��(y��u)С�f����֮��Փ���Mһ������ЦԒ���º���Ҫ“�b”��ʲô�ӵ�ЦԒ������“��(sh��)ǧ��”?���ߵ��^�c�ǣ�“��ֲ‘�bٽ��(y��u)С�f��(sh��)ǧ��’�����b����‘���x’��”��Փ�ď����ׂ������^�m(x��)Փ�C�@һ�^�c����һ�����w���Ͽ����ږ|�hĩ������w��ˇ�У�ֻ��“���x”�ſ�����“��(sh��)ǧ��”��ƪ������ЦԒ���¶��ܶ�С��������ı����Ͽ��������w��ˇ�У����x����Ҫ“�b”�ģ���ЦԒ������ֻ��Ҫ�v�f�����������ZԴ�Ͽ��]��“��”�hκ�x��“��”��“��”�c“��”ͨ��“���f”�c“��С�f”��ͨ���r�˶���“���f”�����x�Q“ٽ��(y��u)С�f”�������x�ɷQ“ٽ��(y��u)С�f”�����ģ����Z�x�Ͽ��죬�hκ�o�Q����С�f�ߣ���“ٽ��(y��u)С�f”����ጞ�ЦԒ���¡���С�f�c����(li��n)ϵ�������DZ����Ժ���¡��C��������ԓՓ�ĵó��ĽYՓ�ǣ���ֲ���bٽ��(y��u)С�f�������x�������x����ͨ��С�f����Դ����ˣ��t�Ї�ͨ��С�fʷ�����Ї�С�fʷ�͑�ԓ��������
����������ƪՓ�Č����x�Ŵ�С�f��Դ���ϵ��Pϵ��Փ���m��\��һ������һ����ͬ�c���Ǿ�����С�f�ɞ�һ���������w֮ǰ���c���x����ǧ�z�f�|���������f��������һ�w�������Pϵ��С�f���w�������xĸ�w�������ͷ��x�����ġ���ԓ�f��С�f���w���еĔ����ԡ�̓���ԡ������Լ��ꐡ��䏈�����ȵ����o�ַ������Ǐ����xĸ�w���^�����ġ���������ČW������ʽ�l(f��)չ���ڂ��ČW�u�u˥�䣬С�f��uÓȥ���x“�b”�����c������ԪԒ��С�f��Ȼ�����v�f�ĺ��E��
����(��)�ڃ�(n��i)���}���ϵ��Pϵ
���������I�ڡ����x�İl(f��)�F(xi��n)�����ČWʷ���x��һ�����ᵽ�ˎׂ����ӡ��ػ͌�������һƪ���J�����x���\ �D�ġ���һ���ֺ͵��IJ����c����ƽɽ��Ԓ�������d���������ɏӛ�����f���w�ơ��Z���L��������ơ����x�r�ڼ�ڣ�����ġ������ܕ�����һ�t�Ɏ����v�b��“���B�Q̫��”�Ĺ��£����ɢ�Y�ϵȵ����w�������Д࣬����һƪ���x���@�t�����������Ե�“؈�Q̫��”ĸ�}��ǰ��һǧ���ꡣ�����վ��ġ����Ӵ�����˃ɰٶ��t���£����҇������һ����ƪС�f����ԓ���е�һЩ���£����@�����v�b���s�x���|����122
�����K�v�����ɝh�������x�c��С�f֮�l(f��)�����J�飬�������xֱ�ӳɞ�Ŵ�С�f�}�ĵā�Դ����29�������e��“�������”��������“�������”��������Ҋ�ڝh������Ů�������塶��(ji��)�x��·���﹝(ji��)�D�����x��顶�����sӛ��Ҳ�d“�������”���¡������o90������K�|���h����������ĝh��ľ���У����F(xi��n)�ˡ���Ů����(��ͨ�x)�����x��ƪ���������Q���W�߂��Ɯy����ʹ�����ġ���Ů�������DŽ�����Ů������ȫ���������������п�����b�IJ��ֹ��¡���ˣ�����Ů����Ҳ�S���r�ͽ���“�x”��Ҳ�������҂������x�����x�����⣬“�ƴ����|���x�w����С�f�����ɿߡ��鹝(ji��)�c�|�h���ߵġ������x�� ����ơ�����·���桷 �鹝(ji��)�c���h˾�R���硶�����x�����ƣ����ƶŹ�ͥ������䛡��еġ����A���ˡ�������“�����������xֱ������������һƪ����С�f”����30�K�v��һ����Ҳָ����“�h���������x�c�Ŵ�С�f�ڄ�(chu��ng)���}���ϵ��Pϵ�����džη���ģ�ijЩС�f�Ĺ���(n��i)��Ҳͬ�ӳɞ�����o�x��(chu��ng)�����}��”����30
�����R�����ġ��ػ����x�c�Ŵ�С�f�Pϵ�о����t�������������졢����܊���}�ġ���ӛ�茑��������־����Ů�g���茑���棬Փ���˶ػ����x�������Ŵ�С�f��Ӱ푡����硶�n���x�������ؑŮ������С�f����ʮ��ŭ���ٌ��䡷�����������Ӱ푵ȵȡ�
����(��)��ˇ�g��ɫ�ϵ��Pϵ
����1.���x�w���f
�����������ڡ�̽�����x����׃��ۙ——��Փ�ػ����x�c�����ČW�����J�飬���x�w��С�f�����������Ƃ����^��T�õ��ַ�������С�f�����ɿߡ���ͨƪ����ZԊ�x���ɣ���Ѹ�����Q����“ʼ��֮��������”��С�f���Ƃ��桶��������������졷��������ū���ȶ����x�w���ĵĬF(xi��n)�����������ڡ��ƴ�С�fʷԒ�����u�r�@Щ�Ƃ�������“Ԋ�P”֮���ּ�“�x��”������(ɢ��)֮�����s����w�����x�w��С�f����r�����������m(x��)����С�f�в���һЩ�x���ɞ��x��С�f�е���һ�N���á����⣬��ԪԒ����������һЩ�xٝ������“��Ҋ��”��“�˵���”��“�ǕrҲ”��“��?zh��n)���”��“����”��“��Ҋ”��“����”���~�Z�������Á����L�����b�硢������B(t��i)����Ȼ���¡��¼��B(t��i)�ݵȣ�������Ⱦ�����á���ɢ�w�fԒ�ЊA����w�xٝ���������˺���Ԓ��С�f�г��õ�һ�N�ֶΣ�Ҳ�ɞ��҇�С�f������ˇ�g��ɫ��
����2.̓����
����̓������С�f���w����Ҫ����֮һ��С�f���T�NҪ�������x���Ѿ߂����ӡ��K�v�ڡ���ǰ�ɝh�������x�c��С�f֮�l(f��)����һ�����f��“�����߂���С�f�������졢�鹝(ji��)�O�úͭh(hu��n)���茑��������Ҫ�صĹ������x����‘Ԣ�Ԍ���’��‘�������’�Ĺ��ܸ��鏊��”��28Փ�ď��@��������Փ�������x�е�С�f���أ��������������췽�棬�������xͨ�����ÔM�˻����ַ����O������ı��F(xi��n)��ʽ�������鹝(ji��)�������Ժ�������Ҳ�ǹ������x������֮һ���h���������x��“�С�f”������߀�w�F(xi��n)���{٩���o�������䏈��̓���Ԕ��·���……�@������S��С�f��(chu��ng)���ṩ�˽��b����28
�����R�����ġ��ػ����x�c�Ŵ�С�f�Pϵ�о���ҲՄ�������x��̓���Ԍ�С�f��Ӱ푡�Փ���J�飺“̓�����x����С�f��ζ������Ҫ������֮һ��”��Փ�ď������̓�����鹝(ji��)��̓���ɷ����Մ�@�����}�������̓�����棬�����e�������x����������������������̓�������ģ�������������ͨ�r(n��ng)��Ļ�����ͨ�^��ȸ�����¼���¶���r����ĺڰ��档����С�f������ӛ���������S־�����ȽԳ�ɫ��ʹ��̓����������N��������Ҳ�Ǐ����x�м�ȡ�I�B(y��ng)�����鹝(ji��)̓�����棬�����e���n���x���������n�i��DԹ������֮���ˈ������ʹ���������x�����ڸ��ԉ�Ĺ���L���ɿô�䣬�����B���~�ཻ���@Щ������������̓���Ե��鹝(ji��)����ʮ�֝���С�fɫ�ʡ�
����3.�ꐡ��䏈�����o�ַ��Ă���
�����x�w��һ����Ҫˇ�g�����������ꐡ��űȺͿ䏈ʮ��ͻ�����@�N�ַ�������С�f�ı��F(xi��n)����ҪӰ푡��������f��“�x�w�ČW���H�ǴٳɹŴ�С�f�γɵ�����֮һ���������ꐡ���������ˇ�g�ַ���߀���V�����뮔�rС�f�Ą�(chu��ng)��֮�С�”���R�����t��Ҫ�xȡ���ȡ����űȡ��������M�˺Ϳ䏈�N���o�ַ���Մ���x��С�f��Ӱ푡��ڡ������x���У������ό������ӷ�D�ͱ��ɐ��ӵ��Sȸ�γ��r������;���n���x����“�JȔ�еأ��G���Ѕ�;�����а飬�������p���~�M��ˮ����������;��ȸȺ�w�������P�ˡ��������֮�ޣ���������֮�D��”���x����֮�����������˹��ĸ��顣�����͔M�˄t߀���ԡ������x����������ӣ��o�٘��;�䏈�t�ԡ���D�x�����������Ќ���D�ij������˿䏈�����o�ַ���
�����������Y
�������w֮�g���P(li��n)�о��_���Ǻ��Ѓrֵ�����x���n�}�����x�@�N���Н���Ї�������ɫ�����w��С�f���Ї��vʷ�ƾá���(n��i)�������Ӳ���׃���l(f��)չ�����w����ײ�ĕr�����Юa(ch��n)���ɴ��о���̽���Ć��}���Ӷ����Ѓrֵ�ˡ�
�����P�����x��С�f��Դ���ϵ��Pϵ���е��о��߱��^���ص��J�����x��С�f��һ����Ҫ��Դ֮һ;���е��о��߄tʮ��ͻ���Ե�ָ�����x���Ǯ��r��С�f�����С�f�����ߟo�ɰ����x��С�f���H���Pϵ���ø�����Ҫ���Դ�����}�о�������x���_���¿��ŵİl(f��)�F(xi��n)��������x���ij����͡��n���x�������ij���������(j��ng)�Ƅ��^���x�о����Mչ���о��߂���ԓ���úìF(xi��n)�еĂ����īI�͵��¿��Űl(f��)�F(xi��n)���^�m(x��)�����о��@Щ���}��
�����mȻ���x��С�f����֮�g���H���Pϵ��֮��������Ŀǰ�ƺ���Ȼȱ��ֱ���C��(j��)�C��С�fÓ̥�����x֮ĸ�w�����С�f�Ķ�Դ�f��Ȼռ���������x�ı��l(f��)�F(xi��n)�������˂����о����r�g�ж̣��о��пɴ������顣�����ţ��S�����x��Խ��Խ����о�����ҕ�����x��С�f֮�g���Pϵ���д��������֮�r��
����ע�
������ �����I.���x�İl(f��)�F(xi��n)�����ČWʷ���x[J].�͵��W��(����ƌW��)��2009(6)��118.
������ �����I�������桢���|�ӡ������е��˷քe���@�N�°l(f��)�F(xi��n)���xȡ����“СƷ�x”��“��Ԓ�x”��“���g�x”��“���x”.���“���x”�����Q�����N�ČWʷ�������ܶ�������.
������ ��Ⱥ.�h�����x�c�Ї��Ŵ�С�f�l(f��)���о�[J].��Փ�W����2009(5)��116.
������ ��Ҋ�۵�117퓺͢ٵ�119�.
������ ���R�ޣ���ƽ.��ֲ�bٽ��(y��u)С�f��(sh��)ǧ�l(f��)��[J].�ČW�о���2013(5)��137.
������ �K�v.���ɝh�������x�c��С�f֮�l(f��)��[J].��������WԺ�W��(����ƌW��)��2011(4)��29.
������ �R����.�ػ����x�c�Ŵ�С�f�Pϵ�о�[D].�Ї������W��2012��46.
������ ������.̽�����x����׃�zۙ——��Փ�ػ����x�c�����ČW[J].�Ͼ�����W��(����ƌW��)��2010(2)��63.
���������īI
����[1] ��Ⱥ.�h�����x�c�Ї��Ŵ�С�f�l(f��)���о�[J].��Փ�W����2009(5).
����[2] �����I.���x�İl(f��)�F(xi��n)�����ČWʷ���x[J].�͵��W��(����ƌW��)��2009(6).
����[3] ������.̽�����x����׃�zۙ——��Փ�ػ����x�c�����ČW[J].�Ͼ�����W��(����ƌW��)��2010(2).
����[4] �K�v.���ɝh�������x�c��С�f֮�l(f��)��[J].��������WԺ�W��(����ƌW��)��2011(4).
������x�ڿ����A�Ŀ���
�������A�Ŀ��š���Ҫ�l(f��)��ȫ��������Ұ���Űl(f��)����ͺ�����(j��)������Űl(f��)���Y�����ČW�gՓ�ġ��g�ĺ�̽ӑ������Փ�c���������£����P����ƌW���g���o�����Փ�ĺ��Y�ϡ�������2004�������ڿ�������2008������ڿ���䛡���ȫ����(y��u)����ƌW�g��Փ�ڿ����Ї���������ƌW�����ڿ���
���PՓ��